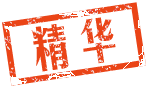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静默禅师 于 2024-11-3 09:13 编辑
写给红袖文学——谨以此文献给红袖天涯曾经70,80后的才子佳人们,愿这篇草原题材的爱情故事能温暖我们的心。 呼伦贝尔的雨 苏子从日本回到草原的时候是个细雨绵绵的秋季,接到她的通知,我匆匆坐上去伊敏苏木的客运班车,在临近窗外的座位上静静的看着路旁的草原,看着远处路旁洼地的巨大积水变成了草原上的水泡子,浸泡在水中的的蒙古红柳一簇簇的,使劲生长着顽强的生命力着实让我感觉到自然的伟大。此时我闭上眼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路旁的积水似乎让我 想起了蒙古族歌手玛希的《道特淖尔》 神奇的道特淖尔晶莹闪光 深情地铺在草原上 沐浴群鹿哺育着牛羊 青草鲜花吐露芳香 道特淖尔在歌唱 歌声诉说着人间沧桑 日月轮回曾有欢笑迷茫 歌声悠悠岁月长 美丽的道特淖尔清澈明亮 静静的躺在草原上 亲吻着蓝天拥抱着牧场 青山伴你送夕阳 道特淖尔在歌唱 歌声诉说着人间沧桑 日月轮回曾有欢笑迷茫 歌声悠悠岁月长 古老的道特淖尔恩情长 安详的展现草原上 陪伴牧人滋润着四方 浪花迎送南来北往 道特淖尔在歌唱 歌声诉说着人间沧桑 日月轮回曾有欢笑迷茫 歌声悠悠岁月长 岁月长…… 远处的山披着一层绿色,在氤氲的雾气下显得那么迷人,造物主是多么的偏爱人类,可人类无尽的欲望,包括心灵的肉体的还有莫名的欲望,对自然的破坏乃至人类自我的戕害是多么的愚昧无知。苏子还是穿着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短款皮夹克,从我认识苏子开始在他模糊的记忆里她似乎对牛仔裤和短款皮夹克有特殊的爱好,甚至她还有绿色,白色的皮夹克,而且她从不涂抹口红之类的化妆品,可上苍还是赐予了她娇好的容貌,属于那种最典型的古典美女,苏子读书的时候我曾经静静的坐在她身旁仔细端详过她,她从不会脸红,平淡的就象秋日里草原上一湖淡蓝的水。 苏子:你今天没喝酒我挺开心的,我回到中国完全是按照我母亲的意愿回海拉尔探望下达斡尔族亲属,同时回来伊祭拜下索然,我还想在苏木 陪索然的父母呆上几天,了却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说完苏子白皙纤细的手指轻轻的摸了下头发,这习惯性的动作还是没有改变。 苏子突然抬起头望着我幽幽的说:“当然,这次我回来对你来说又要接受一次痛苦的回忆,我并非想折磨你,从哲学意义上来讲有因必有果,因果关系我不想从哲学角度来给你阐述,我知道你也读铃木大拙初级的禅学著作,我作为一名学者能准确的分析出你想用禅学排解你内心焦躁不安的矛盾和痛苦,毕竟那些你面对的痛苦只有我能理解,事过境迁我们还是依旧平凡如初,唯一我们和索然的区别,她安静的躺在地下而我们在雨中呼吸着空气走在曾经熟悉的山路上,我们是幸运的,所以要珍惜一切还有必要忘记一切。” “你是日本间谍”我有些半开玩笑的和她说着。 苏子:“你错了,严格来说我从不把四分之一大和民族的血液当回事,我只不过是历史制造的产物而已,我的达斡尔族姥爷姥姥只是最普通的牧民,在昭和战争末期看到我母亲被遗弃在日本水泥房子里嗷嗷大哭,坐在马车的他们听到哭声蹑手蹑脚的来到屋子里,把我母亲抱到马车上飞速离开,你也知道那个年代死亡的概率很大,普通百姓只为了生存而已,我猜想两个牧民是出于善良的天性更是出于家里男孩子太多家里缺个女娃,所以我姥爷姥姥就把我母亲抱养回去。” 我沉默着,像草原一样沉默。 山下的草原草色一直延展着,眼前这秋后的草原逶迤绵长颜色如同秋天葡萄酿造的琥珀色的美酒流淌在大地,天空瓦蓝高远只有几朵白云飘飞,耳畔是秋虫的喁喁,鼻间是草丛树木散发出的清香。苏子扭了扭身子走到我身边轻轻坐下,这古典美女的眼神总是让我感觉天籁中人也是自然造物主修缮的尤物,她习惯性的又摸了下头发轻轻朗诵道:“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我说:“秋天这个意境你用范仲淹的宋词来表达其实也没有错误,你应该用俳句来说出你此刻的心境,怎么用宋词呢?我的心情是让我想起了《静静的顿河》中格里高利和他的情人相拥看着远方,那场景是多么的凄美,反正你离开草原已经很久了,我感觉你变的陌生了,还有就是你当年想在学术上建功立业达到顶峰造诣远渡日本真的那么重要吗?”。 苏子坐起来使劲拍了拍屁股,抖落了牛仔裤上的草屑大声说:“年轻时候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别提了,陌生的原因是我已经离开草原太长时间了,闻着这味道还有看你喝酒的样子让我感觉到了一丝温暖的回忆。” 我沉默着,像这大山一样沉默。 沿着山脊我们一前一后向山头爬去,连日的大雨让灌木丛变的更加繁茂,枝杈阻碍着我们前行的脚步。 “还是我在前面走吧,这样你能省些力气” 苏子笑道:“我在日本也经常爬山的,你也知道我生活中没什么不良嗜好,我和你的先祖都是草原和森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因遗传让我们适应自然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你走在我后面的时候目光不能老是在我的臀部上打转,这样对你的身心健康不好。” “哈哈,苏子屁股有眼睛,我头次知道” 苏子平静的说:你这样的玩笑让我想起了几年以前我们在山头玩耍奔跑调笑的情景,真让我有些想起了索然。 苏子在半山腰突然停下来脚步 ,回头看看我,眼角却是流着泪水:“你帮我去那几颗树下采些稠梨子,不用太多,我只是想起来小时候索然也会给我采很多,你去给我摘一些。” 半山腰崎岖小路上我不时搀扶一下苏子,脚下的烂泥踩着让人感觉很是不舒服。 苏子:“索然死之前你俩见面了吗”?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打断了思路,脑海开始浮现出少年时的画面…… 老徐头喝着闷酒嘴里不停的絮叨,这个身材魁梧的汉族老人一直在巴彦罕草原五头山上生活,因为索然亲叔叔的关系老人暂时让我居住在他这个草筏子盖的屋子,二扇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是拼凑起来的,厨房一个红砖搭建的灶台,旁边放着一个已经被熏黑的木头架子,不知道的什么时候刷上的红油漆已经斑驳掉落,架子里盆盘碗筷收拾很是洁净,还摆着一排有草原人当时最喜欢的月亮门二量二的酒杯,有几个酒杯有了些裂纹,看来不知道那个牧民远道拜访过来,徐头把大塑料壶里的白酒在月亮门杯子子里给倒的满满的,牧民用手指弹下敬天敬地然后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进去,第二杯在满上就要和徐头使劲碰下杯然后在一口喝完,第三杯以后开始慢慢的吃肉然后慢慢喝着酒交流,时间似乎在酒杯里流淌着而屋外的荒野也似乎变的更加寂寞。这个时候索然和我总是飞速的吃完手把肉,然后索然会很有礼貌的用蒙古语和牧民们告别,不打扰这几个饱经草原岁月沧桑喝酒闲谈的牧民们。 老徐头很冷静的说:索然,你不要带他骑你的马,你俩可以走着去那片山头。 索然微微一笑也很淡定的回答:叔叔,这次我俩只是走走,真没想走远。 杭盖心里感到徐头的言语中透着一丝威严或者一丝暗示,或许他在警告索然和我不要做一些逾越的事情。 云彩静静的一抹飘在天边,巴彦罕草原的夏天短促而又炎热,回到小屋子时候牧民们早已离去,小屋子里徐头的鼾声大作,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始终孤独的住在巴彦罕草原的深处,他的身世是是逃亡者还是隐士我充满了好奇。 我擦擦头上的汗水,咕咚咕咚喝了不少凉奶茶,把索然喊道屋外细声说“徐叔睡着了,这个老人年纪这么大自己独居在这里,沧桑而又充满神秘感” 索然眨了眨眼睛,嘴角撇起一丝高傲用蒙古语跟我说:“这个叔叔可不是普通人,你这样的小酒鬼,他会用拳头打飞你的”。 索然杏眼一瞪使劲的踢了一脚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喜欢打听那么多,我不跟你玩了”。 我没有回话一直缓步向山岗上的孤树走去,身后传来索然的声音:“小酒鬼等等我呀,你是不生气了呀,不是吧,等或我给你唱歌,你现在给我站住背我上去,我累了。” 我在山腰停步索然趴了上来,她双手抱着紧紧的贴在脖子上,软软的身体靠在我的背上,鼻尖传来一股女孩身体特有的芳香,我没多想,使劲背着索然山岗上走去。 我和索然并排坐在最高山岗石头上俯瞰着这片草原,阳光照在索然的头发上,头一次才发现索然的头发是黑黄色,闻着淡淡的发香,头次感觉我已经是这片草原的主人,感觉这草原上的牛马,青草,石头,哪怕是块牛粪都是属于我,不知哪里来了勇气,轻轻的摸着索然的头发…… “对不起,老提起当年往事,对你是种刺激” 我:“没关系的,她从呼和回来的时候在海拉尔见了一面,我们喝了很多酒,聊天当中知道她在那边发展的不错,至于她的丈夫孩子家庭情况我没问,问多了反而彼此会尴尬 ,人有些事情还是停留在过去比较好。” 苏子:“她的车祸死讯是我在海拉尔的亲属告诉我的,听完我一天没吃饭” 我:“我是在聊天时从朋友口中得知的,听到她的死讯我脑子一片空白,手颤抖额着连烟都没点燃,人其实太脆弱了” 苏子:“我理解你,我也不想多说,可我在这山上看着我们曾经一起玩耍熟悉的不能在熟悉的景色我忍不住还是想起了她。” “没事,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些痛你不说出来或许更痛,索然死之前我俩的确争吵了一次,晚上我还做了奇诡的梦” 苏子瞪大了丹凤眼了:“什么奇怪的梦,说来听听。 “是奇诡的梦,汉语里奇怪和奇诡意思相差的太多的,我在这荒郊野外讲我恐怖的梦的你不怕吗” 苏子轻轻的又抚摸了一下头发望着我说到:“怕,在着野外你讲恐怖的故事的确是怕,可从小到大你也不是第一次了,每个故事我都是耐心的听完。” “我曾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喝多了祸不单行,你也知道我和索然的关系,索然对钱的概念从小没有,后来她开始骗人,开始学坏” 苏子:奇诡的梦,真是这样吗? 我忧然说道:“晴空万里的湖边芳草连连,远处连绵的青山掩映在碧蓝的湖水中,在湖旁我和索然静静的在自然道上相遇,路旁的马蹄莲盛开着蓝色的花朵,偶尔蓝色的蜻蜓飞落到上面,像往常一样我腾挪跳跃试图上前去抓个蜻蜓哄索然开心。”梦中索然悠悠的叹了口气“不用了,我会考虑我们之间的事情,也许你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了”。此时话语扎伤了我柔软的心脏,正当我心万分悲戚时,乌云已笼罩大地,群山似乎已沉在湖泊之中,我看见很多很多草原上各民族的人走在自然道上,乌云压顶大家开始奔跑。突然从人群之中跑出一个带蒙古帽子的矮个子青年大声喊我,循声遁迹他却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应该回去了,于是他喊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的黑面孔的司机带着我就上了一辆面包车,我匆忙上了这辆面包车,透过车窗我看到刚才涌动的人群早已不见,索然孤零零的就站在路边,她身后那平坦的丘陵变成了层叠的青色山峦,雾气氤氲似乎还下着小雨,我能清晰的看到远处的道路旁有蒙古栎在生长,我使劲抽搐着冷汗淋淋当我醒来的时候被子已经湿漉漉,我赶忙下床打开灯,颤抖的手想从烟盒里拿出一根香烟,可手抖动的很厉害索性我把烟盒丢的远远的,说实话我怕脑子在尼古丁的刺激下我晚上又该失眠了。我索性找到地上撇的罐装啤酒打开一个使劲往嘴里灌了下去,已是夜半我不禁感觉索然就站在我的窗前似乎轻声的在诉说着什么,我又不敢去想,又不得不想。” 苏子突然打断了我的诉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并非你我能左右命运,何必自责。想想这青色的蒙古高原,你我的先祖曾驰骋于马背之上用洪荒之力逐鹿于草原,而你我却在这里伤心于友人的故去,实在是没有广阔的胸怀”。 我:“能不想吗,有些事情发生了,远远大于我心灵所能承受灾难的尺度,我并非是什么英雄,也并非什么狗熊,我只是生活在草原上得一个普通却心灵敏感的青年人,我也想拥有爱情想建功立业,可这些似乎离我越来越远” 苏子使劲吐了口水提了下裤子说道:“你要学会忘记,加油呀,登上山顶我们还得加把劲。” 我低头看了看不远处土庄线绣菊灌木丛盛开的是那么的纯白,不禁低声和苏子说道:“妈的,这花丛真白真像你们那个部位,记得我刚刚知道男女差异的时候,我偷偷跟随你俩去树林里,我看到林子里有俩白色巨大的花脸蘑,我一阵喊白蘑菇白蘑菇,你俩满山遍野的拿着柳条子追我,那个时候我们是多么快乐和轻松,青色的蒙古高原上有我们成长的足迹,是草原的乳汁哺育我们长大,白云和苍茫的山峦让我们曾经拥有过无比的欢愉,似乎苍天永远眷顾这我们,后来发现命运这个东西是无法琢磨的”。 我走到辽山楂灌木丛旁边摘下一窜红色的果实轻轻的递给苏子。 我一下子坐在木桩上翻了翻背包拿出一瓶白酒拧开瓶盖咕咚咕咚灌了下去,白色的液体呛得我剧烈咳嗦着喉咙一松我使劲吐了出来。红的黄的白的在地上一小滩让几个蚂蚁使劲在我的胃液中挣扎着,苏子平淡的望着我,表情中没有一丝惊讶,淡淡的说道:“难为你了”,然后打开她的背包拿出纸递给我示意我擦干净,这个在呼伦贝尔出生后来在扶桑生活的女子很是优雅,不会像普通的妇人喋喋不休的指责或者表现出一些肤浅无知的举动。“先天的秉性和后天的教育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吧”,我脑海里闪动着这样的想法,这个我最好的朋友曾经和索然形影不离的女子,青少年时代我们一群草原的孩子沿着海拉尔岸边一路向南走着,沿途我们高歌蹦跳,可如今我们望断天涯也不能在相聚。 那年奇冷的冬天索然从牧区为了来到镇里去送下即将出国的苏子毅然从冬营地骑上马奔袭几十公里,那一片银白下索然的身体在零下40摄氏度是如何承受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一直是我心中的疑问,还有人类情感中莫名的疼痛,霜天白雪掩映下无尽的苍茫草原一骑一人受着侵入骨髓的寒冷时而奔跑时而缓步,贝加尔针矛枯黄的枝干已被积雪掩埋三分之二以上,山坡上樟子松林显得那么阴郁,在冬日阳光下她和蒙古马只能和时间去赛跑,如果索然在夕阳西下之前找不到海伊公路,在漆黑的夜里很可能会迷失方向最终失温晕倒在马背上,或是蒙古马驮着她原路返回冬营地,可那样命运完全交给了长生天。 当索然推开我们屋子时候,身上厚厚的蒙古袍上已全是是白色。衣服很多地方已经冻成了僵硬的冰棱,她熟练的脱下蒙古袍,把身上头上的御寒的东西一件件的摘下去分开放起来,如同一个老渔夫在湖面上清除鱼的内脏一样,熟练而又有特殊的动作。 她使劲的揉搓着手说着“酒鬼,求你去把我的马拴好,给它添上草,记得不要给它喝直接打出来的井水” “苏子,你抱抱我,看我现在多像刚出土掩埋在冰封荒漠中千年的那个女子,我是感觉那么的冷”,说着脸上露出了调皮的笑容。 “酒鬼,我是不是这片草原上最棒的女子,在路上我想如果我晕倒了,我的马会驮着我返回冬营地。如果我被冻残了,我的父母会多么的伤心,你会哭吗?我想起了你给我讲起过拔都汗西征的故事,我想着想着有了勇气。 从回忆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苏子一个人已经登上了山顶眺望着草原,一切还是那么静谧。 苏子终于叹气缓缓说道:“考虑下和我出国吧,那边的事情我会一手操办,我看你在国内很不开心,还是和原来一样嗜酒如命,一定还是不断地出现着这样那样的故事,可能你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不想追问发生了什么,理由就是随着老去我们都累了,余生你还可以给我讲讲故事,这些年其实我也想通了,有些事情我太倔强,年龄越大我也和你一样开始信命,在过几十年都是轻烟而已,还有什么想不通”。 我:“这事算了吧,我年纪不小了实在是不想折腾了,母亲老了身体也不是太好,留在母亲身边,她能得到不少安慰,别的真没什么值得留恋,再说索然知道我们走在一起会骂死咱俩的,我做不到你那样冷静,一切都是命,就是好朋友的命,你从小骂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镇里的小癞蛤蟆不想吃天鹅了。” 苏子:“又开始犯胡侃的老毛病,哎,你心里想什么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的,晚上你可别偷偷哭呀,我不在你身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没事,很多事我现在已经麻木了,也不是我一个人麻木,很多人在琐碎中麻木,媒体上说的星辰大海大概是火星上的吧,和普通人没关系?这些年身旁的人和事换了一茬茬的,建筑物变了,马路四通八达。唯有咱们小时候玩耍的草原上碱泡子没变还是那么大,连周围的坟地都被搬迁给活人挪地方了”,呵呵,死人都被折腾一遍,我算什么呢?” 天上的云开始从远方飘过来,越积越多,山雨即将到来。 苏子:“快下雨了,赶快下山,索然父母一定在煮肉,在故乡的土地上和你还有叔叔婶婶吃肉喝酒会让我感觉幸福”。 我:“喝多了不许哭呀,也不许闹,更不允许那样”。 苏子:“你个混蛋,本姑娘啥时候那样了,你呀,就是没正形,可我就喜欢你这样,说来也是个天大的笑话,这几天时间你一定要陪着我看看家乡的一草一木,”。 我:“那是自然了,我也有很多心里话和你说”。 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们安静的朝山下走去,偶然我看到山路旁一簇簇叉分蓼生长的很旺盛,想起我和苏子的分别,心情跌入了谷底,山路上留下我们的足印不久将被雨水冲刷干净…… 2024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