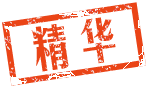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古韵今风 于 2025-5-12 19:02 编辑
有个女孩名叫小兰
一.有女如是 小兰三十多年前就出名了。她的出名有两个原因,一是漂亮,二是神秘。
那时没有电视,市里唯一的一张报纸上登的都是造反派战报。这些东西和张家桥巷里的人们没多大关系。他们只对身边一些细琐的事感兴趣。比如谁家包了馄饨送给××家一碗啦,谁家的孩子捉迷藏掉进了马桶里啦……新闻播报是二十四时滚动式的,而乔小兰总是头条。 张家桥巷人一说起她就得意得不得了,好像在炫耀自家的闺女。 美的东西总有引力,何况生香活色。家有适龄男丁的无不想娶她来当媳妇,没有儿子的恨不能她是自家的闺女。
男人们很怪,对美到了极点的女人反而心生怯意,畏若神灵,不敢有半点非份想头。窄窄的巷子里,只要遇上小兰,他们总是客气地为她让路,连大气儿不敢出。哪怕平时对老婆凶神恶煞似的男人,此时也堆上卑贱讨好的笑容,尽可能地谦恭。
然而张家好婆另有理论:“你们阿晓得,这种女的讨回去只能像菩萨似的供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家?她又是什么样的人家?”
张好婆的关子卖得有水平,大家伸长了脖子等她下联。可是她又偏不说了。
啊?小兰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疑问像弄堂风一样刮遍了张家桥巷。他们的话题转移了,不再是小兰的漂亮而是她神秘的出身。
对啊,这母女俩见了人只是点点头,从来不停脚步的。
张好婆肚子里一定有故事,非常好听的故事。大家相信这故事的可靠性,就像朱鸿兴的碗面一样货真价实,味道醇美。
1967年那会自来水金贵,附近几条巷子只有张家桥巷口有个水笼头,人们都拥在那里等候,挤得要命。倒是有个半瞎的人专门挑着木桶卖水,水面上浮着块木板,可送到家只剩了大半。所以张家桥巷的人家一般都吃井水。谁家有口井真是稀罕得不得了。小兰家的天井里是有口井的,别人都不能进去打水,唯独对门的张好婆。足见他们之间的交情了。再说,张好婆老少几代在这条巷居住了近二百年了,小兰家的细枝末节都逃不过她老人家眼去!
可是她偏不说。真是要命。
什么东西捂久了都要发霉变味。人们听不到真凭实信只好瞎猜。有人说,这是个大户人家。你看,整条巷子就她家是三层青砖大楼,望进去进深得很。数了数窗,估计有十几个房间呢。对于大户人家的说法大家是一致同意的,可问题是,她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呢?开钱庄开店开厂还是那个大家说不出口的营生?为什么这么大的家只有母女俩?小兰她母亲怎么是单身?离婚还是丧偶?她们是上海口音,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有人煞有介事地分析,文革初期,红卫兵没有抄她们家,证明成份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是什么资本家,地主,汉奸,反革命。大家尽可放心,该怎么就怎么。可是有儿子的人家到底还是不放心,必须盯紧这家人,看看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
他们不是福尔摩斯,谁也没猜到:兰花开在梨园里!这是张好婆实在气不过说出来的。这是有根据的。张好婆的表妹曾经是小兰祖父的跟班。 这个信息幸亏不是公开在文革初期,不然这乔家可要倒大霉了!戏子的身份当时在大家眼里和婊子差不多,多半会被红卫兵挂了破鞋示众的。
好婆原来算盘打得好,这个孙媳妇是要定了。凭什么?就凭好婆捏住了人家的软档!之所以瞒着大家也是为自家的声誉着想。但是从那夜起她就觉得没必要了。 那天深夜,夜黑得可以捉鬼。她睡不着,也不开灯,站在门口瞪着对门的小兰家——既然是我未来的孙媳妇就得当心她——这女孩也有24了,出落得神仙似的,危险哪。 好婆早就鼓动孙子去追了,可这小子居然不敢。要她亲自去说。她还没想好怎么去说呢,却是出事了,是大事!
好婆看到她和一个又矮又小的男人站在三楼卧室的窗前,对,那是小兰的卧室。灯影里,两个影子忽而叠在一起,忽而分开。好婆看得发昏。
两条新闻像两颗原子弹在张家桥巷爆炸了,冲击波几乎要掀掉每间屋顶。人们碰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知道,知道,那个小兰她妈是戏子的小老婆,小兰交了个歪瓜劣枣般不三不四的男朋友!”
……闲言碎语像夹着碎玻璃的龙卷风刺喇喇盘旋在小巷里。对小兰,男人们的眼里没了敬畏,女人们的眼里没了羡慕。
二.众相无相
小兰丝毫没有察觉张家桥巷人的情绪变化。
为什么会和苏勇谈恋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爱情是个复杂的东西,有生理的,心理的,道德的,审美的多种因素。但是,它发生在兰儿身上的主导因素却很简单——寂寞无助。
从小到大,小兰衣食无忧,也没有受人欺负,可就是缺少玩伴和异性的关爱。小兰从来没见过爸爸。只知道家里的开销都是他每月寄来的。他是省会的京剧团团长,一个风流人物。一妻四妾,子女有十多个,小兰妈是第三房。小兰没有嫡亲兄弟姊妹,妈妈又不准她和邻居的小孩玩。而大学里的男同学都把她当白雪公主,胆小的不敢追她,胆大的又吓跑了她。
妈妈长得很美,标准的瓜子脸,三重睑,也就是三眼皮,秀气挺拔的鼻子,明目皓齿。小兰像妈妈,但比妈妈更漂亮,皮肤又白又嫩。兰儿知道自己很漂亮,可漂亮有什么用?就像花园里那枝孤零零的红玫瑰很寂寞很无助地开在墙脚边。
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新指示下达后,各行各业运作起来。负责分配工作的女人是个正派虔诚的老阿姨,她认为,像小兰这种娇小姐就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打掉点傲气。漂亮怎么了?空壳而已。佛说,众相无相。
结果,小兰被分配到了废品回收站,和破布头,空瓶子,旧书,废报纸等等打交道。每天,她系着围裙,戴着袖套,秤那些五花八门的破烂。
苏勇来了,夹了个破棉絮来了。来得时候不情不愿,走得时候容光焕发。他居然在一个臭烘烘的废品回收站里发现了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自此,苏勇跑废品回收站好像跑商业中心。他娘觉得奇怪,这小子近来怎么勤快起来了?好是好,就是过分了点,明明还可以用的东西也被他当废品卖了,比如那只钟,秒针断了有什么关系呢?
苏勇有两个哥哥,都是市里响当当的造反派小头头,不幸的是,亲哥俩参加的派别却是死对头:一个是踢派,一个是支派。何为支派呢,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支持革命委员会的就叫支派,反之叫踢派。
支派占据了城里,踢派只好下乡。别看这里是江南水乡中国历代出状元最多的地方,可人一旦眼睛发了红就顾不得儒雅斯文的乡风了。就拿这哥俩来说,只要踢派弟弟潜回家被支派哥哥发现准会打起来,从家里打到巷里。
苏勇哪派也不参加,用当时的话来讲是逍遥派。一门心思就想讨个漂亮的老婆。
想不到无意中撞见了小兰。
小兰觉得这个人太讨厌了,一会儿拎个破锅,一会儿卷个破被,一趟趟地跑来。小兰每次见他来,总拉着个脸,一副不耐烦的表情。苏勇并不介意小兰的反应,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曾经偷偷弄来“破四旧”没烧掉的书来看,知道有个千金一笑的故事。他还无数遍地研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相信,人心不是铁打的,总有芝麻开门的时候。
苏勇每次来不急着走,他抢着帮小兰整理、转运每天收购的废品。无数次无数天。到后来,他一天不来,小兰倒奇怪了,心里竟有些牵挂。
一天,苏勇拿了只藤椅来,说,别坐在旧报纸上,上面有很多细菌,对女孩子不好。又从裤兜里掏出两张电影票,说是内部电影《清宫秘史》,问小兰去不去。小兰很想去,可又觉得不妥,期期艾艾地说:“我,我回去问问妈吧。”苏勇一脸决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撕了它!”作势要撕。小兰急了,这票难弄得很啊,撕了多可惜!忙说:“别别,别撕啊,我去我去!”苏勇认真地说:“一定很好看的。”“可是,我……我从来没单独出去过啊。”看小兰很为难的样子,苏勇说:“你就说和同事一起去的好了。”
小兰妈犹豫了一下也还是答应了。姑娘大了,也应该有自己的社交。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苏勇为了这一半耗了整整一年。现在他想收网了。纲举目张,这纲在妈妈手里呢!苏勇妈今年60岁,在居委会当副主任。老于世故,人情练达。
当他把底牌亮出来时,全家大吃一惊:“什么什么,你小子居然敢花隔壁张家桥巷的巷花?!”苏勇妈恍然大悟:“怪不得家里的东西一样样少”。“妈呀,你那些破铜烂铁值几个钱,美人可是金不换哪!”“妈,下来的事我不懂,听您安排了。”“当然,你娘可不是吃素的。嘿嘿!”老太如此这般地吩咐儿子,苏勇频频点头。 苏勇是个孝子。从来妈说一他不会说二。如果妈不点头,小兰哪怕真是天仙也是断断进不得家门的。
那边欢天喜地,这边却人仰马翻。
小兰把她和苏勇约会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惊讶了半天,回过神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想都别想!一个破工人,臭体力,家里穷得剩个破床,你金枝玉叶似的,般配吗?你若要去,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女儿!”
小兰犟道:“妈,您也不想想现在是啥辰光,还没看够戴高帽子游街啊,还要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工人怎么了?现在无产阶级最吃香了。他们家三代工人,咱们家是什么成份呀?爸爸演了那么多才子佳人的戏,要不是这里的人不知情,咱们家早是封建余孽了。有这么太平?”说着,眼圈红了。
妈妈默然。
小兰又说:“只要他对我好就成了,我长这么大,除了您疼我,还有谁啊?”
“这事还得问你爸。”妈妈口气软了下来。
“我爸!我爸!我不知道我有爸!”
“啪!”一记耳光刮在了小兰脸上。
“你这么可以这样说!”妈妈怒道。
“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我连影子都没见过他!”
小兰妈叹了口气,立马委顿下来,不再吱声。
小兰捂住脸说:“妈妈,我不怪您打我。我知道您心里苦。”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
“他不是乱搅和的人,你看他什么派也不是,平时也不多话,只是默默关心我帮我。他没有勉强我,是我自己要和他好的。”
“让我见见他再说。”
“可是他妈妈说要先见我呢。”
“瞎说!真是不懂规矩。哪有姑娘先上婆家门的?!革命也不是这么个革法。可见他们家粗俗!”小兰妈好看的脸气得绯红。
小兰低了头,说:“知道了,妈。”
“阿姨。”
小兰妈恹恹地点了点头。
分明看不起我嘛。苏勇打量了一下小兰的家,明白自己在小兰妈心里的地位了。哼,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了。不过,政治太远了,当然没老婆要紧,何况现在还没到手呢。他把手里的网袋举得高高的,对小兰说:“你拿到厨房去吧。”
小兰妈有点不好意思了,笑笑说,谢谢,让你破费了。
苏勇前脚走,妈妈就说,人倒还老实,就是太穷,太难看了。小兰说,现在还有资本家地主啊?大家都靠劳动吃饭。我们年轻,穷是暂时的。难看嘛……这个,众相无相。小兰想起了那个老阿姨的话。
三.情是九月霜
小兰站在苏勇妈跟前,羞红了脸轻轻道:“阿姨好。”“好好好。”苏勇妈上前拉了小兰的手疼爱地说:“姑娘啊,你家的事苏勇都告诉我了,我两夜都没睡着觉,我心疼你呀,都怪我们家苏勇认识你太晚,让你多受苦了。那个断命的回收站怎么是你这样的姑娘呆的地方啊,派你去的人真是瞎了眼!孩子,闺女好,闺女贴心啊,可怜我生了三个光浪头,他爸死得早,我连说个知心话的人都没有。”说着,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吸了下鼻子又说:“现在好了,有你了。好闺女。以后咱娘俩有伴了。” 小兰不知道,真正疼人的老太太不是这么能说会道的。她一下子被感动了,一把抱住了苏老太,一声妈脱口而出。
苏老太破涕为笑:“啊呀,好孩子,听你一声妈,我睡梦里笑出声啊,苏勇,愣着作什么?倒茶啊。” 小兰脸红了,刚才应该叫阿姨的。但也不后悔。
老太说:“孩子,你坐啊,我弄菜去。”
小兰说:“我帮您。”
“呵呵,不用不用,今后日子长呢。”她把小兰推向苏勇:“儿子,你们说说话,带她看看咱们的家。”
苏勇家自然不能和小兰家比,平房,一共三个房间,老太太住了一间,老大老二合一间,苏勇一间。这是在知道苏勇有了女朋友后才调整的。
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你觉得我们家怎样?”苏勇问。
“嗯,不错,你妈也不错。”
苏勇一把抱住了小兰。
小兰妈给苏勇定了个规矩:白天不准来。说巷子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会嚼出蛆来。那天晚上,苏勇和小兰亲热了一下,被张好婆看见了。结果全巷子的人都知道小兰有个长相难看,鬼鬼祟祟的男朋友。
那时结婚是不能摆筵席放鞭炮的,认为是搞迷信活动。 蜜月是甜蜜的,就好像吃一桌美食,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等到酒足饭饱,发现外面在下雨,公共汽车挤不上,打的又舍不得,浑身淋得湿漉漉的,到一小店避雨,又被店主埋怨妨碍了他做生意。你想,心情会怎样?
筵席是生活的点缀,而生活就是一堆麻烦,一地鸡毛。
第一根鸡毛已经飘落在地。
那天晚饭后,老太把小兰叫住了:“兰儿呀,你们已经满月了,也该正经过日子了。你也知道,这个家男人多,他们都是油瓶倒了不扶的东西。就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年纪不轻了,时常腰酸背疼。今后家务就交给你了。”小兰愣了愣,也是,女人要做家务啊。她说了声,好的,妈。抬脚要回房,苏老太又叫住了她:“你要交饭钱啊,工资准备交多少?”“30元行吗?”小兰工资是35元,想自己留点买些女人用的东西。“32元吧,你们不能顾自己啊,还有两哥哥没结婚哪。”小兰有点不高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她是新媳妇,和为贵嘛。她默默点点头,说:“妈,那我过去了啊。”
小兰把婆婆的话告诉了苏勇,他笑笑,打了个哈欠,说:“累死了,早点睡吧。”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小兰第一次感到了这个男人的冷漠。
家务劳动不外乎三件事,三餐,洗衣和打扫。后两样到没什么难的,小兰在娘家也做。煮饭倒也容易,可是这买菜炒菜小兰还真是不会。
没多久,每到吃饭,全家人的脸色就难看了。有的夹了一筷刚送进嘴里就吐了出来,有的伸长脖子吞药似的。老太太对于菜难吃倒是没说什么,就是天天埋怨菜买得又贵又不好。有一天小兰终于忍不住了,回了句嘴:“妈,我实在不会弄,我和苏勇另吃吧。”
老太光火了,腰也不疼了,一下跳到大门外,挥着手臂,拉开嗓门就喊:“你是我婆婆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来了没几天就要分家啊,不得了了,造反到真正的造反派家里来了!我是吞了你的钱还是伺候小姐你不够啊……大家来听听,这是什么道理!”
……梗子巷的人都盯着这家人的仗怎么打下去。可是奇怪得很,刚拉出的架势转瞬就化解了。就像突如其来的大火又被突如其来的大雨给浇灭了。灭是灭了,细心的人还能闻见烟味看见烟。他们再看不到苏勇和小兰成双作对地出门了……小兰心事重重,脸上失去了光泽,看人似乎像没看见,还有人注意到她的腹部在隆起。
小兰是个不会吵架的人,没那个心机也没那么丰富的词,最多是骂声有毛病。苏勇根本不理他了。两个大伯子看见她也只作没看见。可以说,这场战争没开始小兰就输了。输得很彻底。
现在没人帮小兰弄那些废品了,还糊里糊涂怀了孩子。苏勇是在她睡得糊里糊涂时爬到她身上的。听天由命吧。
当然,菜还是小兰买,不过是婆婆烧了。小兰轻松了些,可胃也随着轻松了。本来,等她下班后烧了菜大家一起吃的,不会吃不到。可她现在真是吃不到了——等她回家他们早吃好了,就剩点菜汤。为了孩子,她忍住眼泪,把残汤浇在饭碗里,闭着眼吃下去。
那天吵架后,苏勇根本就是当她死人,一直不理不睬。母亲态度不变他也不会变的。小兰几次回家想对母亲说自己处境艰难,可又说不出口。当初是自己要嫁的。
小兰妈看到女儿萎靡不振的样子只道是怀孕的缘故,倒也没往别处想。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张家桥巷的人议论纷纷。
张好婆说,看看吧,这个丫头讨回去好不了,人家回娘家是成双成对的,她经常一个人溜回来,也不见丈夫来接。哼,一定是好吃懒做得罪了婆家。边上一片附和声。有人接口道,我看那男人也不是东西,不管怎么样,她怀着你的孩子呢。好婆阴阳怪气地哼道,这就难说了。什么难说?有人问。张好婆又不说了。
张好婆抛了个话头,喜欢热闹的张家桥巷的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传到后来,说是小兰有个姘头的,人长得非常英俊。大家觉得一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然如花似玉的小兰会嫁给这种人家?说不定是怀了那姘头的孩子,姘头甩了她,才不得已嫁给了这个三等残废。他们是六只眼睛拜堂的!
这话到底还是传到了小兰耳朵里。她对母亲说,我住了也有半个月了。吃过晚饭我回去。小兰妈心疼女儿,埋怨说:“这苏勇怎么回事,也不来看看你,连我这丈母娘也不放在眼里。”小兰说,他忙呢。那我送你过去?不要了,我没事。
小兰拖着身子,懒懒地走到家门口,拿钥匙开门,发现锁被换了。 客厅灯亮着,她举手想敲门,听见婆婆说:“走了就别回来了!”另一个声音好像是婆婆的弟弟:“不孝媳妇守孝堂。”接着是有人拍桌子砸东西大声叫骂,其中有自己的丈夫。 一屋嘈杂。 小兰堵着耳朵往回走,到自己家了。抬头一望,妈妈房间的灯还亮着。
早上7点钟,张好婆照例去乔家井边打水,忽然杀猪般叫起来:“井里有个人!”
|